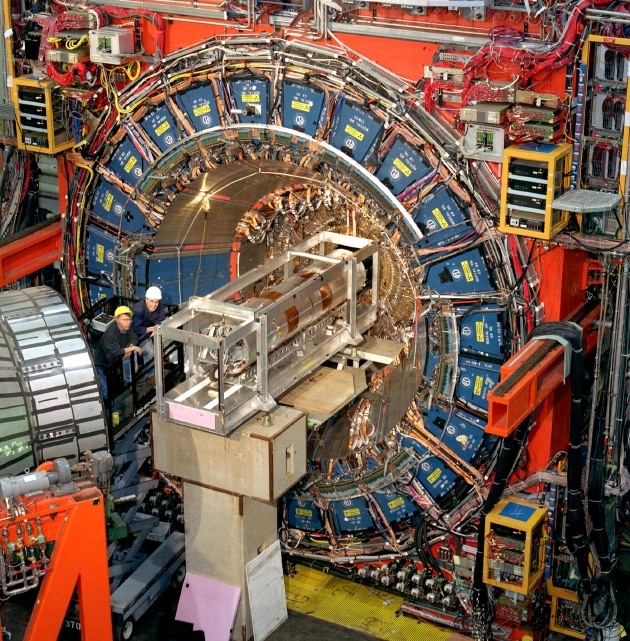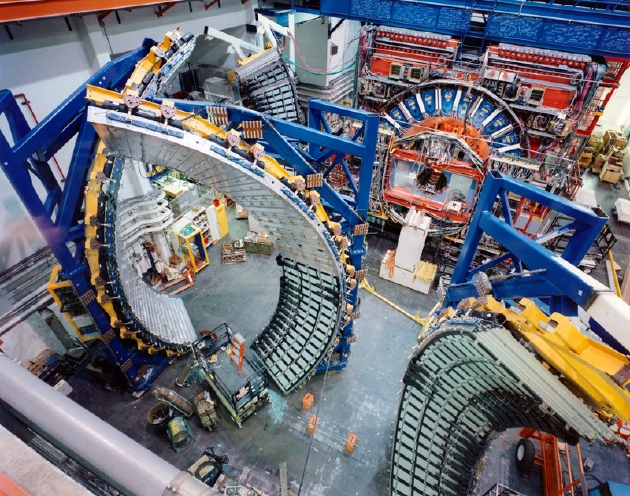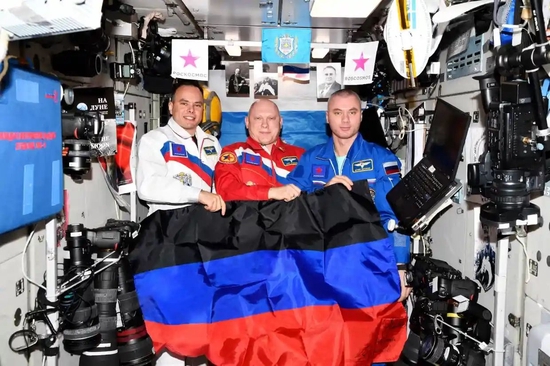科学大家|粪便有力量!修复地球的“代谢断裂”

作者:丽娜·泽尔多维奇(Lina Zeldovich)
出品:新浪科技
编译:任天
作者简介:丽娜·泽尔多维奇(Lina Zeldovich),记者、科普作家,著有《另一种暗物质:变粪为宝的科学与生意经》(The Other Dark Matter: The Science and Business of Turning Waste into Wealth and Health)。
每年秋天,当喀山灰色的天空乌云密布,雨水连绵不断并开始变成雪花的时候,祖父就会在我们小小的家庭农场中忙碌起来,为迎接苏联漫长的冬天做好准备。他穿上结实的工作服,戴上沉重的手套和大靴子,走向化粪池,那里存放着我们家全年产生的污水。他打开化粪池沉重的盖子,将两个旧桶拴在结实的绳子上,用好几个小时将池子里的东西转移到农场的土地上。放学回家时,我就能确定祖父在一英里外进行着一年一度的下水道维护。那种气味飘得很远,四处弥漫,与秋天的其他气味——腐烂的树叶、湿漉漉的狗和人们为过冬而熏烧的猪油——混合在一起。
尽管气味浓烈,但我从未对这种气味感到厌恶。相反,我对祖父的整个行动都很着迷。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每一季都会发生一次——就像新年前夕,我最喜欢的节日。化粪池每年只打开一次,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而祖父是唯一能触摸到它的那个人。祖母不允许我靠近化粪池,因为她害怕我掉进去。当我穿过荆棘丛和荨麻,准备向化粪池走去的时候,她就会出现在门廊上,就像一个从瓶子里出来的精灵,朝我尖叫着“马上回来!”。我愿意付出一切,去看看这个化粪池系统神秘的内部结构。我渴望看到它砖砌的内脏,里面应该满是棕色的粘稠物。但此时此刻,我只能在远处观看祖父的魔法。
祖父有一套自己的污泥分配系统。他从不把桶装满,这样当他把桶提起来时,里面黏糊糊的粪水就不会溅到靴子上。有时他用手提着桶,有时则用木头扁担把两个桶挑起来。他在番茄地里戳了几个小洞,把粘稠的粪水倒进去,再用泥土盖住。地里的番茄已经干了,不用担心果实会被粪水污染。他还往苹果树和樱桃树的根部倒了一些粪水,耙了些叶子盖上去,这样当我们四处走动时,脚底就不会沾到了。他还在一个堆肥坑里倒了一堆污泥,和其他有机垃圾混在一起。堆肥坑是大自然孕育“黑金”的地方,也自成一个系统。
农场里的三个堆肥坑是按轮作时间表运行的。在整个生长季节,堆肥坑里堆积着我们所有的有机垃圾——枯萎的花朵、拔除的杂草、枯萎的黄瓜藤茎等。厨房里的剩菜也被倒了进来,比如土豆皮和发霉的面包。在这一季结束时,祖父会在坑里混入污泥,然后封闭起来,在几年时间里让其腐烂分解。两年后的春天,当祖父打开堆肥坑时,所有死去的和发臭的东西都不见了。坑里满是柔软、肥沃的泥土,散发着大自然、春天和下一次收获的希望。新形成的土壤松软、轻盈,就和糖粉一样,只不过是黑色的。植物的根喜欢这种土壤,我也喜欢。把柔软的土壤握在手里,再把小小的绿色番茄苗种进去,这种感觉真好。我已经闻到了这些幼苗的淡淡清香,不久之后,它们将开满鲜花,结出香甜的红果。

祖父曾说,“你必须像养活人那样养活地球。”在我看来,这句话简直太美了,充满了大自然的智慧。我们向地球索取,因此也必须有所回馈。这里的夏天很短,凉爽多雨,但在祖父的果园里,草莓从6月开始变红,番茄一直成熟到9月。我们的苹果树和樱桃树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春天芬芳,秋天美味。对我来说,这就是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排泄物与这种循环密不可分,就像我们人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一样。排泄物不是丑陋的污秽,而是来自我们体内的高效肥料。
甚至我们的语言结构也暗示了这一点。在俄语中,肥料被称为udobrenie,是dobró的衍生词,意思是好的和丰富的。因此,常见的关于厕所的笑话也围绕着这个概念。当我的小表弟们在接受如厕训练时,我们就说他们需要去排一下dobró或bogatstvo(表示财富)。那些住在大型公寓楼里的人没有化粪池,但我肯定,他们的“财富”也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土壤里。如果不施肥,地球就不能永远地有所产出——它将变得贫瘠。我原来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当我长大后——政府拿走了我们的农场,我们移民到了美国——我很震惊地发现,大多数人对他们排出的代谢物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排泄物去了哪里。他们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此外,他们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冲水,然后忘掉,问题在于,地球无法处理所有这些排泄物,尤其考虑到我们排放它们的方式。我们的排泄物正在让地球窒息。
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每天产生大约半公斤的粪便。这意味着纽约市(官方人口普查数据超过800万)每天排出超过4000吨的粪便。东京略高于此,每天4150吨。现在想象一下,地球上70亿人在24小时内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堆粪便,再乘以一年365天,那将会多么惊人!
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粪便?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试图与其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这个过程的具体机制取决于你所生活的地方。在西方国家,我们把粪便从厕所里冲走。在不那么幸运的地方,粪便会被留在坑厕里,或是在树下分解。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或文化背景下,人们都想离粪便越远越好。我们普遍厌恶粪便。这是屎,我们的排泄物。从定义上,粪便令人恶心,在视觉和嗅觉上都很可怕。
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粪便意味着危险。如果任由大自然自行处置,一堆粪便几乎马上就会危及人类。病原体会被粪堆里的营养物质——氮、磷和未消化的蛋白质——吸引而来。有的以其为食,有的在里面产卵。当粪便物质进入饮用水时,会导致霍乱、痢疾和肠道寄生虫的传播,导致致命疾病的爆发。因此,人类与自己的排泄物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游牧祖先处理得很轻松。他们会在休憩的时候留下危险的排泄物,然后离开。然而,当人类定居下来并开始农业耕作时,就再也不能把粪便弃之不顾了。于是,人们开始把粪便堆积在坑里,或者倒进河里。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一些祖先就学会了如厕后冲水——苏格兰的斯卡拉布雷保留了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迹,当时的居民建立了原始形式的冲水厕所。古罗马人建造的公共厕所,座位已经与我们今天的厕所类似;这些无用的东西会落入排水沟,由不断流动的水通过污水管道将其带出城墙。中世纪欧洲的居民建造了用桶来储存粪便的厕所,之后这些桶会被密封起来,埋在地下。
然而,当人们开始聚集在城市中生活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事实证明,向本地水体倾倒排泄物是危险的——上游居民不仅污染了下游邻居的饮用水和洗濯水,还引发了疾病暴发。19世纪和20世纪初,臭名昭著的霍乱大流行席卷欧洲,罪魁祸首便是饮用水的粪便污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即使在今天,腹泻病每年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约82.7万人患病和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估计更为严峻:每天有2000多名儿童死于腹泻病,比死于艾滋病、疟疾和麻疹的儿童总和还要多。在发达国家,人们建造了冲水式厕所、地下管道和巨大的污水处理厂,以保护自己不受巨大粪堆的伤害。然而,这些现代工程奇迹对地球生态造成了重大破坏。
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或“地球营养物质的再分配”,但从概念上讲,这与我祖父的“养活地球”的观念是相呼应的。你可以想想自己的食物来自哪里,你会意识到,很多食物都是在其他地方种植出来的。随着香蕉、苹果、生菜、玉米和水稻的生长,它们从土地中汲取养分。然后,这些食物被卡车、轮船、飞机运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吃掉它们,然后排泄出来。但我们不会像我祖父那样,把这些有机物送回原来所在的地方。我们不会通过开车、驾船或乘飞机的方式,将这些有机的馈赠归还给土地。相反,我们就只是把它们冲进下水道。
我们的污水处理厂会清除污水中的病原体,但不能清除其中富含的氮、磷和钾。这些强效肥料通常会流入附近的水体,不断地给湖泊、河流和海洋提供过量的养分。这会导致有毒藻类的大量繁殖,最终使鱼类死亡,水体衰败。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些水体并不能吸收如此多的肥料化学物质。同样地,没有了人类的“养活”,我们的地球从生物学的角度也无法继续生长粮食。
因此,由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粪便运回食物的来源地,这个星球的营养物质再分配过程就一直持续着。土壤变得贫瘠,于是我们开始使用合成肥料,而这远不如真正的粪便,而且生产过程也会造成很大的污染。在摆脱“危险的暗物质”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自然母亲的基本规律和法则。通过将人类的粪便从这个等式中移除,我们不仅改变了农业,还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生态。
修复这一断裂的链条对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健康都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将粪便运回食物的来源地。事实上,我祖父不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一些更节俭的古代社会早在我们之前就发现了这种生态智慧。很久以前,粪便是很受欢迎的,我们也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可以学习。
1737年,中国清朝的一位皇帝(乾隆)颁布了一部官书,规定所有的臣民都要努力收集自己的排泄物并加以利用。粪便被戏称为“夜香”,因为人们通常在凌晨把夜壶放在门外,由挑粪夫收走。在江南,收粪是一项蓬勃发展的业务。与此同时,中国北方人对此并不热衷。这种差异相当惊人,北方“街道不净,地气多秽”;而北方人“须当照江南之例,各家皆置粪厕”(《授时通考》卷三十五)。书中这一段的开头有一句话,既平淡又充满诗意,那就是“惜粪如惜金”。
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善于收集粪便是有原因的。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就位于中国南方。杭州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人口超过300万。另一个大规模扩张的城市是长江边上的苏州,人口为650万。所有这些人都要吃饭,因此农民必须种植大量的农产品,每一点肥料都十分宝贵。如果没有人粪,农民可能就永远无法种出足够的粮食。正如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好粪》(The Good Muck,2017)一书中解释的那样,收集粪便是一项重要的事业,也是一份非常受人尊敬的差事。在这本书中,沃斯特讲述了中国的“粪便史”。
收集粪便的人被称为“粪夫”,他们推着手推车穿过城市的街道,把居民家马桶里的粪便污物倒进重约60磅的木桶里。每辆手推车可以装下6到10个木桶,累计重量可达600磅。那些想要进入这个行当,但没有能力买一辆手推车的人,可以从肩挑木桶开始——就像我的祖父一样。粪夫每天收集粪便的路线,以及将粪便运出城的路线都是指定的。他们将粪便装进小船,盖上稻草以消除臭味,然后运到乡下。在那里,城市里累积的代谢产物经过处理,根据其价值摊开、干燥和分类。并不是所有的粪便都是平等的。富人的粪便卖的价最高,因为他们吃得更好,排出了更多的营养物质。穷人的粪便则售价较低。能够负担得起的农民选择了更昂贵的肥料,因为这可以种植出更好的农产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粪肥就是金钱,农民们也像对待金钱一样来对待粪肥,甚至将其储存在防盗容器中。既然是惜粪如惜金,那也就必须像保护黄金一样保护人粪。
在日本,人粪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以黄金来衡量的。例如,根据日本学家苏珊·汉利的说法,一两金币可以买到足够一个人吃一年的粮食。与此同时,十户家庭一年产出的粪便价格被定为半两金币。据东京立教大学的田岛夏与教授介绍,人粪在日语中被简洁而恰如其分地称为“下肥”。在快速发展的大阪和江户(今天的东京),这种“下肥”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管理机构必须制定一个严格的权利和监管体系。例如,如果一个家庭租了一间房子,那么谁拥有粪便的权利——房客还是房东?产出粪便的租户本应自豪地成为自己粪便的主人,这似乎合乎逻辑,但前工业时代的日本立法者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将珍贵的下肥所有权授予房东,房东将粪便卖给收粪者,再由后者卖给农民。在某些情况下,农民与城市粪便生产者建立了直接交易的合同。城市居民向农民承诺出售自己一年内生产的所有粪便,以此换取一定数量的大米作为预付定金。心存感激的农民有时会赠送礼物,比如特制的大米点心,有时就被戏称为“粪饼”。
较为富裕的农民会与大名建立联系。大名是日本的封建领主,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仆人,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下肥”。农民们为大名的庄园提供了柴火和用作菜园的幼苗,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优先收集大名最优质“下肥”的权利。大名及其仆人们都吃得很好,因此他们的粪便营养非常丰富。
日本农民为收集“下肥”而相互争斗并不罕见。1724年夏天,有两个村庄就爆发了“粪便战争”,争夺从大阪不同地方收集粪便的权利。作为回应,城市居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监督粪便交易和价格谈判——并且提高了粪便的价格。一些较穷的农民发现,自己陷入了很糟糕的境地,因为他们再也买不起肥料了。这导致了一种以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犯罪:偷屎。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行,执法部门将不少重罪犯送进监狱,但这并没有阻止绝望的农民铤而走险。
同样是人类的排泄物,这些社会为何会演变出如此不同的看法?答案就埋藏在地下。与拥有茂密森林和绿色草地的欧洲国家不同,日本没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这个国家贫瘠的沙质土壤无法自然地生产出丰富的农作物。在一块新开垦的土地能够产出食物之前,农民们必须努力工作,用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点生物质来滋养它。日本有句古话说,“新开垦的田地收成薄”。只要人类还存在,“下肥”就是一种很容易获取的自然资源,永远用不完。日本人利用自己产出的肥料,将不容易耕作的多石土地变成了肥沃的田地。同样,中国农民世世代代都维护着肥沃的土地,这在欧洲农民看来,简直堪称奇迹。欧洲和美洲的农田或早或晚,都会变得尘土飞扬。
这种现象十分有趣,以至于美国农业科学家富兰克林·希拉姆·金恩在1909年前往亚洲,研究所谓“永久农业”的秘密。回国之后,金恩写下了《四千年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1911)一书,提出了一些有关如何施肥的建议。然而,粪便事业可能太过令人震惊,无法在美洲大陆腾飞。经过一个多世纪,这个想法的种子终于萌发,变成如今被广泛讨论的“循环农业”概念。我们的人粪可以修补,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填补由我们造成的严重的代谢断裂。
在环保主义者当中,让人粪回归土地的想法无疑正在生根发芽。然而,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克服许多现实挑战。城市居民会将他们的陶瓷厕所换成夜壶吗?他们会把夜壶放在门外,让排泄物和垃圾桶里的其他垃圾一起被收走吗?以及,污水处理厂会将城市污水泵入驳船,然后运往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使那里的农田变得肥沃吗?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可以适用于每个地理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种对下水道污泥进行升级利用的方法,来修复我们所造成的营养物质再分配问题。令人鼓舞的是,其中一些方法已经开始实施,有的是小规模的试点操作,有的则已经实现工业规模。
总部位于英国和马达加斯加的初创公司Loowatt几乎完全遵循了日本人利用“下肥”的策略。该公司派遣了一名服务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从当地的贫困社区收集粪便。这些粪便先是保存在厕所下方的可生物降解的袋子里,然后被密封并收集起来,再加热以杀死病原体,最后装入生物分解器。在那里,大量的微生物会像在我祖父的堆肥坑里那样,将粪便分解并变成堆肥。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也会释放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沼气。Loowatt的团队就通过燃烧这些甲烷来加热粪便,形成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另一家位于海地的初创公司SOIL Haiti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用今天人们的“下肥”来修复该国被消耗和侵蚀的农田。在水资源缺乏的地方,人工收粪是一种高效、廉价的卫生解决方案,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保持城市清洁和养活地球。
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弥合“代谢断裂”。加拿大Lystek公司使用巨大的搅拌器将下水道污泥搅拌后,用卡车运到乡下,注入田间——这是一种机械化的方式,取代了我祖父将棕色粘稠物倒入土壤的做法。DC Wa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将粪便再利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华盛顿特区及其周边地区生活着220万居民,当他们的代谢产物送到这座工厂时,会被装入巨大的高压锅中,在149摄氏度和6倍大气压下沸腾,这将杀死其中所有的生物。之后,这些产物被倒入巨大的混凝土生物消化池中,喂养饥饿的微生物。最终的产品包括用于发电的甲烷和一种黑色的液体粘稠物质。这种粘稠物经过干燥后被包装起来,在当地商店出售——这与粪夫对粪便的处理过程惊人地相似。这种肥料被称为“Bloom”,原料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其外观、质感和气味就像我和祖父在园子里种西红柿所用的土壤。
在远离电网的地区,或者能源成本较高的国家中,个人生物分解器是许多家庭的福音。这种小型分解器由以色列的HomeBiogas公司开发,采用坚固耐用的塑料制成,可以将任何类型的有机废物转化为沼气和液体肥料。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Epic Cleantec公司开发了另一种适用于住宅或办公楼的方案。他们采用插电式装置,对建筑物的下水道排泄物进行清洁和循环利用,使废水不流到污水处理设施,而是可以重复用于洗衣服、浇植物和冲厕所;剩下的具有臭味的粘稠物质则被转化成肥料。
既然有了这么多先进的技术,我们为什么还无法修复“代谢断裂”?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必须修补有关排泄物的意识形态中的另一个巨大断裂——不是代谢断裂,而是思维断裂。与古人不同,我们今天仍然认为排泄物是需要处理的“终极废弃物”;我们仍然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且具有多种功能的资产。我们把许多精力和金钱花在清除危险的污秽上,而不是获取并利用这种由身体新陈代谢所产生的优质产品。身处21世纪的人类社会,我们必须实现这样的思想跨越,才能完全解决代谢断裂的问题。
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暗物质”去污名化。我们必须将其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完全可再生的、可持续的资源,并为自己是这种资源的有力生产者感到自豪——就像历史上那些更节俭的社会所做的那样。我们还必须意识到,粪便可以做成很好的生意,粪便可以赚钱。这种宝贵的财富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抢,而我们却捏着鼻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粪便是我们与循环农业、可持续经济和合理的营养补充之间的最后一道边界。这是人类最古老的GDP,当商人和企业家们再次为谁能拿到这些东西而争吵时,我们就可以确定,代谢断裂已被修复。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