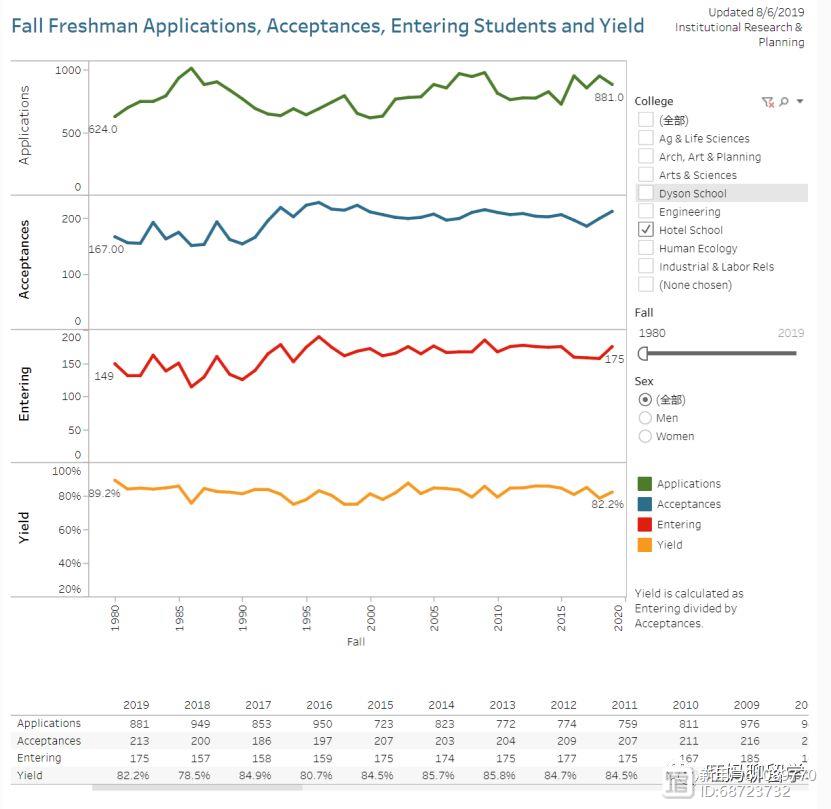免签陆路直达,领略中亚四国的独特风味


——
出境游开放后,越来越多人走出国门,体验几年未曾感受的异域风情。不过当下,部分国家签证难办,机票价格依然昂贵,可供选择的目的地并不多。环球旅行家张海律近期从新疆伊犁陆路出境,免签进入哈萨克斯坦,一路游览了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不开放个人旅游签证),让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云游一番,领略中亚各国的饮食风俗和独特的风土人情。

国门重开,我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陆路出境,到达对中国单方免签的哈萨克斯坦。拼车前往阿拉木图的路上,汽车在加油站停下休息,我去买咖啡,重新刷上停用三年的信用卡。休息区的电视里播着一则有趣的广告——一个人背着行囊,千辛万苦翻越高山草原,疲饿交加倒在草堆里,一个哈萨克汉子骑着骏马到他跟前,递上一块蓝底上印着金色太阳的国旗巧克力。被广告吸引了的我,从货架上拿起一块相同的巧克力,品尝到了置身中亚的第一口滋味。
名字就叫“哈萨克斯坦“的这种国家级巧克力,并没什么特别味道,远比不了甜食发达的欧洲和中东。需要抵御严寒漫长冬日的草原民族,养育出质量不错的牛羊马,在古往今来间,将整片偌大的中亚,塑造成一个味蕾上的“纯肉斯坦”。

迁徙的生活,难以留下独特的料理方式,简单粗暴的烹饪,拼的只能是肉质本身。幸好,那些蓄积脂肪能力强的大尾羊,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我曾在哈萨克斯坦推行转机三天免签那阵,到过阿拉木图。跟着攻略,去到一家名为Gakku的著名马肉料理餐厅。

记得在挂满壁毯和萨满装饰物、布置成牧民毡房的空间里,我点了一大份连带着面条、洋葱和马肠的那仁,感觉没什么特别,至少比不了我在新疆伊宁吃到的同款民族美食。

▲
Gakku民族餐厅的那仁
作为国菜的别什巴尔马克(Beshbarmak),突厥语直译为“五个手指“,大概可以联想为不用刀叉、筷子,直接上手,大快朵颐。剔除里面的面条和土豆,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也就是手抓羊肉。只要食材是一年单胎的大尾羊,那么无论是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还是东边我们的阿勒泰地区,都不用耍调料的花招,只用白水煮,怎么都好吃。

▲
五指面,摄影/武晓慧
阿拉木图毕竟是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国际化都市,既有跟着大量朝鲜裔和俄裔居民生活传统的饮食文化,又少不了丰富的欧陆菜肴和汉堡制霸的街头快餐。这一次令我最惊喜的食物是意面。不像我们的西餐厅一般只有Spaghetti一种细面,阿拉木图有着堪比亚平宁半岛的丰富面种,我最热爱的扁面linguine,没加任何本地化改良地保持着“意味”。
据2021年统计,俄罗斯族裔占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15.5%,随着过去一年的国际局势,又涌来大量临时性居民,安静而低调,同他们的日常餐饮一样。

终于重新出国后,我迫切地希望与当地人交流,需要通过“沙发客”的方式走进人家的生活。

幸运地是,我在阿拉木图与阿斯塔纳之间的工业城市加拉干达,迅速找到了免费收留我的沙发主亚历克斯。这个37岁的电信工程师,与妻子和一对儿女生活在市中心祖父留下的老宅里。早起就到厨房忙碌的斯维塔娜,一边哀怨着自己沦为了家庭煮妇,一边摊出了喷香的薄饼,并告诉我最近一周都是俄罗斯人传统的谢肉节。

▲
加拉干达沙发主家的厨房(左)
煎薄饼(右)
这段又被称为送东节的时间,斯拉夫文原词为Maslenitsa,是古远异教年代战胜黑暗的春女神,人们为此做出象征太阳的金黄色圆饼。东正教信仰来临后,因为大斋戒不能吃肉,人们就抓紧之前的一周时间暴饮暴食,感谢肉食。
这一天是星期三,若严格按着传统,是谢肉节的宴请日,岳母得邀请女婿和客人到家中吃薄饼,酝酿力量,为周四醉酒日的雪橇和拳击做准备。冰河上集体斗殴的壮观场面,可参考米哈尔科夫的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

▲
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剧照
当然,名导将这一传统过于夸大和浪漫化了,现实是,这并非公共节假日,亚历克斯和大多数俄族人一样,都得去上班,而岳母家则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工业区,至于烂醉和打架,“别再把我们想成那样的战斗民族,我只爱喝茶”,切了一段香肠放进奶渣饼里的亚历克斯说到。

从看不清夜色的河景餐厅起身,到前台刷卡结账,115550,没看错,这是一份四大块烤羊排和一杯石榴汁的价格。我掏出手机查询实时汇率,约等于人民币71元。这也是我独自一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的最高一次餐饮消费了。

相比其他几个邻居斯坦,唯一存在完善旅游业的乌兹别克斯坦,交通、住宿和餐饮等旅途消费价格要低得多。这既有经济欠发达的原因,也因为物产较为丰富带来的可选择余地充分,还得感谢旺盛旅游业造成的竞争吧。这个国家从2021年3月起对中国人执行10日免签的政策,但得在首都塔什干机场飞入飞出才作数。想要陆入也简单,电子签证20美元,3个工作日出签。这家餐厅敢在门口立“第一烤串”(Best Shashlik)的英文招牌,至少那份羊排滋味确实不错,入味又有嚼头。可惜,这也是对我而言的乌国美食天花板了。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核心的通道,有着太多名城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在数千年的商贾来往中,留下了中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饮食。简单说来,就是新疆和俄罗斯口味的结合体。然而体验下来,绝大多数时候可以评价为,虽然混搭了油和甜,却变成了两头都不靠的甜腻。

▲
塔什干的那仁
城市里大街小巷都用大锅翻煮的抓饭(Polov),旅游手册自信宣传着:各地区甚至各餐厅的风味都不一样。首都塔什干城北的中亚抓饭中心早已成为打卡景点,迷信周四是最佳受孕时间以及锅底油汁有壮阳功效的本地人,也和游客一样大规模涌来。


但无论有没有机会一展雄风,吃几口就会觉得“呵呵”,跟少了鹰嘴豆、葡萄干的新疆抓饭相比,甜得毫无喷香感了。不想多吃?那就再来一碗常作为开胃汤的拉面(Lagman),外加一两个加了南瓜丝的烤包子(Samsa)。

对当地食物的不适应,当然有地域口味养成的关系,但再细想一步,新疆美味的形成,少不了川湘菜系的融入和影响。中亚市场上香料品种再丰富,没有辣味,始终难对我们的胃口吧。不过确实也听在中国做外贸的当地人自黑,吃过广州的新疆抓饭,再没法接受自己家的。口味勉强差不多的,是同料同法的馕(Nan)和薄皮包子(Manty),即便当地喜欢蘸着酸奶酱去吃,始终也保住了香脆感和胡椒气息。

▲
撒马尔罕的薄皮包子和羊汤
也有不一样的东西,把牛羊肉打碎、混上米饭,裹在菜叶里的“中东粽子”,从地中海东岸到高加索山区,再到阿姆河谷,都很常见,却在新疆乃至整个中国极其鲜见。这其中滋味最特别的,当属用酿葡萄叶作外皮并可一道入口的Dulma。没有此饮食传统却大量产葡萄的吐鲁番,也从曾经拿葡萄叶喂羊变成了如今的喂人。虽然是“低配版”新疆,但在塔什干一天下来,选择倒也无比丰富。起床,可以在街边买肉饼和土豆饼,就着加了盐的奶粥,搞定早餐;中午,逛完巨大而喧嚣的琼苏巴扎,到一侧一长排棚户街市,囫囵吞下烤包子和抓饭;晚上,找一家连锁的民族菜Milliy Taomlar,吃烤肉,两串管饱。

有一晚,我走到1976年就建起的前苏联第一家非国营剧场Ilkhom,欣赏了一出先锋实验话剧。事实证明,文艺和美味从不兼容,或许因为怕油腻污染了精神世界,全世界的文化中心附近,从来都是只能三明治果腹的美食黑洞。从纽约林肯中心、墨西哥城电影中心,到此刻塔什干的戏剧地标,哪都一个样。

相较上述两个斯坦,不免签的吉尔吉斯和塔吉克都需要办理在线电子签证(拒签率较高),更可靠且便捷的办法是,在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塔什干这些大城市相应的使领馆去面签。至少在夏日里,依偎在天山山脉一侧的吉尔吉斯斯坦美得令人惊叹,绝对是中亚的颜值顶峰,不过食物和周围的斯坦兄弟从类别到滋味都近乎一致。酷暑难耐的盛夏,首都比什凯克街头树荫下,能救人一命的液体面包格瓦斯摊位,远比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密集。无论在名为“邓小平大街”的商场前,还是伏龙芝将军的塑像下,没有什么渴是一大杯格瓦斯解不了的,如果还不行,那就两杯。

▲
小城纳伦混搭一切的午餐
凉爽甚至寒冷,随着越来越靠近天山山脉而涌来。伊塞克湖东岸的小城卡拉科尔,是通过徒步、骑马乃至滑雪探索天山的户外大本营,也有着自清末左宗棠平乱后,陆续从陕甘两省迁徙过去、成了被前苏联归类的“东干人”。他们虽然早不能说中文,但凉皮还保留了下来,没陕西的那么酸,冷汁比例也多一些。

▲
卡拉科尔的东干凉皮
对于探险的游人,这个高山草原国度更多的风情和餐饮,都在需要艰辛跋涉才能抵达的牧民毡房里。我在一个中部小村子,找来一位马夫,准备前往深山里神秘的宋湖。两天一夜的马背往返,注定是一趟腰酸背疼的痛苦之旅。只会“Left、Right“两个英文单词的马夫Karma,带上我和在村中做志愿者的德国小伙Aken,开始了这趟颠沛的”屁股苦旅“。

▲
去往宋湖山路上的牧民毡房
Aken的欧陆肠胃显然跟不上自己味蕾的包容与豁达,几小口酸甜的马奶下肚,竟就迅速决堤了。还好,牧民足量的红茶,成了管用的腹泻药,几杯下去后,我们终于能重上马背,向着想象中静谧湖边的落日晚餐前进。

“这顿晚餐搭配真好,荤素均衡,本想着进到山里见不到绿色呢”,丹麦姑娘安娜盘腿坐在地毯上说到。这是我进入塔吉克斯坦的第一顿晚餐,地点是西部范恩山脉七湖区域的一户牧家乐(Homestay)。安娜就职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具体负责食品安全部门在中亚地区的工作,这次出差过来,抓紧时间从乌兹别克斯坦过境,找说英语的私人向导开车载她转两天,恰好就在春雪未融的山里,碰到另一个外国游客——我。“在美国,我确实有些很极端的素食主义朋友,她们是不可能理解这里餐饮现实的。高寒山区没有肉,让牧民怎么活?”当然,食品安全的工作性质会对肉的来源和屠宰流程有所要求,也就让安娜会刻意节制肉类摄入量,即便在中亚这片“纯肉斯坦”。

▲
混搭肉菜的蛋糕
菜比肉贵得多,是中亚国家的普遍现实,尤其在青黄不接的隆冬时节。在哈萨克斯坦做沙发客,赶上俄族人的谢肉节,给我免费食宿,顿顿大肉伺候的房东,最后一日才舍得捞出苹果和青菜。
在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苦盏,正为在这个不刷信号卡、也不支持银联取款的纯现金社会怎么生存犯愁时,迎面碰上一家“乌鲁木齐餐厅”。被门口用粤语“食佐饭未?”跟我搭话的塔吉克小伙迎了进去。一大碗水煮肉片里,竟有着新鲜的莴笋。

▲
苦盏乌鲁木齐餐厅吃到最多的绿菜
从重庆来此开店一年半,并主要为附近中资矿山供应生活物资的老板跟我聊天,并用微信转账帮我兑当地货币,而这也是偏门国家的中餐馆对旅行者最重要的意义。说话间,渐渐知道,在塔吉克斯坦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在挖矿淘金,少部分在搞蔬菜大棚,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吃上莴笋、菠菜的原因,“他们都很赚钱,甚至一年能挣上百万。”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大多在莫斯科打工,条件好一些的会到广州做小本外贸,因此,一路上听到很多操着蹩脚普通话甚至粤语的当地人,对广州美食的花式赞美,包括“水果好多”、“便宜好吃”、“上菜好快”等。

塔吉克斯坦虽以友好闻名,但正规一些的餐饮业,也学西方国家那样,慢条斯理地点菜、上菜、结账,时不时上前问你感觉怎么样?账单包括了服务费。

最后一日,我来到首都杜尚别宫殿般的Kokhi Navruz,参观这座原本想打造为全球最大茶馆,却最终成了国宴接待中心的奢华场所,准备就在里面巨大的餐厅吃饭。

▲
杜尚别市中心餐厅的香肠相较接待过各国领导人的宴会厅,对外餐厅显得有些像烂尾楼了。我点了一串羊肉、一串蔬菜、一碗酸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服务生上前用英文惯性问候,“感觉怎么样?”另一位会几句中文的服务生则不停安抚,“老师,对不起,再等几分钟,不要走。”这顿漫长的晚餐,在服务生追到门口的一句句“老师,对不起”中结束,我离开这个全球最大茶馆,结束了这次悲喜交加的中亚之旅。
——
撰文|张海律 责编|王筱祎
摄影|张海律 部分图源网络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