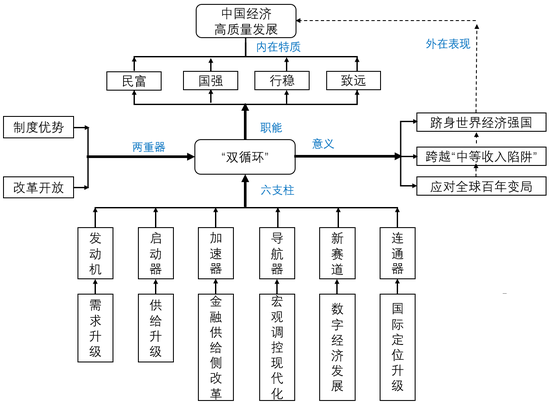如何应对预期的经济下降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南希·伯德索尔(Nancy Birdsall)全球发展中心荣誉教授、高级研究员
COVID-19爆发前,发展中国家未来充满希望。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从2009-10年的大衰退中迅速复苏,其中不少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享受到全球石油、原材料和农业商品需求激增的好处。
美国则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收益都流向了原本便已富裕的群体,中产阶级和穷人日益落后。许多分析师将民粹主义右翼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归因于这些趋势。随着中产阶级的缩水,越来越多的工作阶级陷入了绝望,许多人对全球化导致的就业损失、政府对阿片类药物泛滥视而不见、社保计划资金不足,甚至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本身感到愤怒和失望。
美国上升预期正在结束,在战后数十年的繁荣期中,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既成规范让美国的自由民主体系韧性相对较强。但在本世纪,社会凝聚以及道德进步的分享感开始消退,让国家和人民越来越容易受到反自由民粹主义的影响。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教训。破灭的预期不但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福利,也有害于社会构建和维持民主规范和制度的能力。
总体而言,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比美国更强更稳定。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腾飞,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初跟进,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波增长足够让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1.90美元),但并不能保证他们跻身中产阶级。相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挣扎者”阶级,家庭人均收入在每天4-10美元。
挣扎者比穷人好一点,但他们缺少定期收入和社会保险,因此很容易遭受家庭冲击,如健康危机和突然失业。大部分挣扎者是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心的食品、交通(网约车司机)和零售行业的个体户或非正式工人。发展中国家有三十亿挣扎者,他们既有雄心追求更好的未来,也焦虑于挥之不去的返贫风险。
逐渐地,经济增长让一些挣扎者(最有可能的是一些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成功跻身规模庞大且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人均日薪10-15美元。但是,工作阶级挣扎者家庭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占人口的60%,中产阶级家庭占了另外的20%,极端贫困和富人则各占12%和8%。其中,挣扎者和新中产家庭所面临的疫情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冲击的风险最大。
伦敦国王学院的安迪·萨莫尔(Andy Sumner)与合作者们估算,COVID-19将导致发展中国家2020年GDP萎缩10%,让大约1.8亿人跌入每天1.90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之下。世界银行的估算基于幅度更小、因国而异的GDP萎缩程度(平均为5%),但仍然警告将有7000万-1亿人跌入极端贫困。
对于成千上万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犯任何错误,日子却变得比自己所预期的更差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当敢于发声和提要求的人民遭到预期的猛然逆转时,结果是美式社会紧张和政治极化。2014-15年,拉丁美洲地区增长开始恶化,平均每年不到1%,这意味着人均增长为负。结果,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时能够容忍的条件,突然间不再如此。
此后五年,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大部分是针对官员腐败以及政治和公司精英所享受的内部特权。只有相对情况较好的智利,示威者成功实现了进步变革。
在COVID-19的阴影下,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政治和金融压力。因为没有可交易的本国货币,这些国家无法从未来公民(如美国和欧盟那样)手中借钱满足眼下的需要。
面临社会凝聚下降、政治动荡和专制和民粹主义卷推崇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银行必须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规模更大的贷款项目。这些项目应该简单直接,目标是为即刻现金转移提供资金,以确保贫穷和挣扎者家庭的儿童不会挨饿和永久辍学。这些投资对于获取未来人力资本是不可或缺的,而人力资本则是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
COVID危机标志着美国的自由民主不仅要抵御国内的极权主义,还要为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出声音。如果人们相信前景不再光明,政治就有可能迅速变得混乱,并给自由和公民自由造成附带伤害。
(本文作者介绍: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 0000
- 0000
- 0000
- 0000